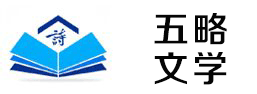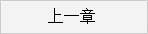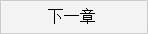重庆南开中学是我的母校,也是我的故园。从呱呱坠地到高中毕业,在此,我度过了烂漫的童年,求索的青年。往事历历,恍若眼前;乡愁于心,似一首首隽永的诗篇。仅以这组散文寄托我对故乡的无尽思念。
南开记忆——我们的父亲母亲
亲如兄妹,比邻而居;我们一个独特的群——南开中学老教师子女。当我们呱呱坠地,新中国正霞光万里;当我们牙牙学语,南开——三中正改换门庭。〔1〕
远去了童年的记忆。当我们“排排坐”在南开幼儿园里,周孃孃、高嬢嬢、任孃孃就是我们共同的“妈咪”。伴着欢快的风琴,当我们舞动小手,撅起小屁屁;我们的父亲母亲正步履匆匆,奔走在三友路上,神采奕奕,板书在范孙楼、芝琴馆——教授着八方荟萃的山城子弟。
沿着同一条小路,当我们背上小书包,蹦蹦跳跳上学去;津南村小学又张开双臂,把我们搂在怀里。薛伯母、于伯母、黄伯母而今虽难分清,但郑老师、孙老师、许老师却依旧记得不爽毫厘。
一年一度,当金银花的馨香,又溢满津南村的夏夜;坐在门前的老槐树下,乘凉的滋味是多么甜蜜。闪闪的繁星,斑驳的月影;牛郎织女的故事,嫦娥奔月的传奇——父母的娓娓讲述,怎不令我们心醉神迷。
暑去寒来,当腊梅的馥郁,又温馨了三友路的除夕;谢师的贺年片,又堆满了父母的案几。清华的二道门、北大的未名湖、南京的天文台、鞍钢的一号炉……也一一进入我们童年的梦境。
名师出高徒,何况是自家子弟:“一脚跨进三中,一脚跨进清华”,我们曾充满美好的憧憬。但——一阵飓风,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竟摧折了满园桃李,也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轨迹。
“批臭老南开”“砸烂孔家店”——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打破了校园的宁静;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糊满了洁白的墙壁。享誉教坛的父母,被斥为“反动权威”;张伯苓的南开群英,被追查“历史问题”。抄家焚书的红卫兵,倾覆了津南村的安宁;“牛鬼蛇神劳改队”的凌辱,摧残了一代名师的身心。
校之不存,家又何依?我们也曾惶惑地跟进,只为取得“红外围”的待遇;我们也曾痛苦地背叛,只为摆脱“狗崽子”的骂名。
静夜家灯,依旧莹莹;却不忍再看父母累累的伤痕,不忍再听父母违心的“鼓励”。
再回首泪眼朦胧:十六七八,二十上下,人生有几个豆蔻年华?四十出头,五十左右,教师有几段黄金生涯?
但——毕竟经历过抗战的洗礼,张伯苓的南开群英,又怎会忘却师者的使命?文革后的三中,百废待兴;我们的父母又老当益壮,重举教育救国的大旗。家里的台灯,几回回彻夜不熄——父亲还在重写被焚毁的教案;食堂打回的饭菜,几次次凉了又热——母亲还在教室解惑答疑。老树新花,三中又熠南开的风采;光前裕后,南开又创新的业绩。
新竹胜旧竹,桃李满园绿。而今,我们的子女已到了而立之际。蜜越酿越甜,日子越过越富裕;书香门第是否还能乐道安贫?
几多思虑,踌躇于物欲横流的市井;几分清纯,保留在弥足珍惜的南开记忆。
注释:
〔1〕:重庆南开中学是由著名爱国教育家 张伯苓先生于1936年创办的。1952年12月,学校由私立改为公立;1953年更名为“重庆第三中学”;1984年5月,学校复名“重庆南开中学”,南开校友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亲自提写了校名。
童年的伊甸园
斗转星移,弹指已半个世纪。当年的南开也曾是我等髫龀小儿的乐园——爸爸妈妈都忙着教学生去啦,我们便和园中的百花一起长大。
啊,南开的百花园,一片一片又一片:桃李湖畔、三友路边,大操场的看台旁、津南村的宿舍后面。繁花似锦,争奇斗艳;许多品种,就连大公园里也难寻见:孔雀花、鸡冠花、老虎花、太阳花、指甲花、地雷花……这一串花名虽不见经传,却寓满小伙伴们自编的童话。
用铁丝草缠绕大树,搭成一座座碉堡——如有巢氏构木为巢;采摘酸汁草、蛇甘蔗,放在嘴里咀嚼——如神农氏遍尝百草。南开的百草园更放飞了我们想象的翅膀。
像群雁在蓝天成行,像鱼群在水中游荡;晚饭后的津南村犹如笑语鼎沸的天堂。家家的娃娃都齐聚在“方场子”上:跳房子、丢手帕、五步猫、拍三下……你做老鹰我做鸡,每个小伙伴都玩得忘却真假。
南开的大操场则是我们的游乐园:其下的防空洞,我们曾数次探险;岩壁的汩汩清泉,我们曾捉到蝌蚪小虾。且不言沙坑里的摸爬滚打;爬杆、荡秋千、双杠、攀登架,我们亦似燕飞猴爬。津南村的“足球小子”已在为世界杯厉兵秣马。
许多记忆,已如流星逝去;有些则像恒星永挂——最亮的一颗,是我和君莉的创意:一粒白胖的花生米,就是一只小鸟;垫有棉花的火柴盒,便是它的窝。一根红头火柴,扎上一束丝线,就是一个“扫把人”——想必安徒生的童话亦由是生发。
谈到创意又倏然忆起:用桂花叶煮制的剔透书签,用铁纱网刷出的精美明信。送给老师,也送给爸爸妈妈——他们都乐得笑开了花。
…………
童年的岁月,寸寸如金;童年的记忆,桩桩甜蜜。穿衩衩裤的玩伴:佩良、亚雄、阿林,晓莉、小平、小津(今天的爷爷奶奶们);音容笑貌仍定格在学前的年龄。
尽管已无路回返,像武陵人迷失了桃源;但梦中仍欢聚在童年的伊甸园。
无声的爱
时光荏苒,五十载倏忽而去,操场、食堂,池畔、花丛……无不闪现一个个鲜活的面容。一些称呼或许显得不恭,但却是忘年交的认同;即便直呼姓名,儿时的我们也是在模仿父母——像对自家的弟兄。就让我再叫一次吧,补上一声问候,一个迟到的热拥:花匠叶华挺、木匠蒙自标、电工徐安庭、龚上学,操场的老韩、食堂的老卓、收发室的“红鼻子”、后勤处的“李保长”、守后门的彭大爷、烧锅炉的赵大叔…… 啊,南开的校工,我们的叔叔伯伯!辛勤的劳作,呵护了童年的幸福;我们的成长,也像校园的花木。
花在记忆中盛开,情在心中澎湃;花匠叶华庭的身影,又闪现在绚丽的花海。蓝色的工装裤,黄色的大草帽;修剪着美丽的绿草坪,浇灌着奇妙的含羞草。他还会对花儿说话,笑眯眯的可温柔啦;他喜欢我们,就像喜欢他的花。不过,谁要是偷偷摘花,他可就变脸了:眼睛瞪得像大老虎,“还要告诉你爸爸”。
后勤的“李保长”也让我们又爱又怕。操场上放电影,广播里找妈妈,哪儿都离不开他;就连我家的饭桌,他也常来检查:“二娃,桌上莫掉饭啰;小毛,碗头要吃干净噻——浪费的娃儿要抓起来!”爸爸妈妈也向着他:“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我们——能不当心吗。
教学楼背后的木工房,则是最诱人的地方——刨花、木屑、锯木面都可拿去过家家。拉大锯的蒙师傅,只不过刮刮我们的鼻子,威严地叫声:“小李!小郭!”听惯了乳名的我们,倒美滋滋的啦——爸爸们也不过被称为“老李”“老郭”么,我们,嗨——走路都更神气了。于是便直呼其大名“蒙自标”,把他当成哥们了。还诌了一段小快板:蒙自标,本领高,拎着工具到处跑;乒乒乓乓修桌椅,就像一只啄木鸟。
大操场的老韩则是我们崇拜的偶像。看台下的储藏室就像阿里巴巴的山洞一样,老韩就像神灯中的大力士——翻筋斗的厚棕垫,跨栏用的大铁架,每天搬一百趟也“不在话下”。一万多平米的沙土操场,都打扫得平整溜光;他的一手绝活更是力贯四面八方:右手握起大铁勺,舀满雪白的石灰粉,躬身、斜臂、疾步如飞。转眼之间,整个操场周圏便划出了,毫厘不爽的标准400米八道跑道。经年累月,不辞辛劳,老韩的“斜膀子”也誉满全校。
食堂的叔叔们本事都倍儿高:泡松松的大馒头直接挑战大面包;辣乎乎的“冲菜”能把眼泪都冲出来。那几年闹天灾,牛皮菜、红苕藤都做成了招牌菜;就连松针、小球藻也磨成了香喷喷的糕。大厨老卓还特能逗乐:俄语большой(大的),他读成“八儿推蓑衣”;овощи(蔬菜),他读成“窝粑稀”。尽管缺肉少油,肚皮也难吃饱;但端起饭碗你都会笑弯了腰。
…………
啊,南开的校工,我们的叔叔伯伯。尽管从未登过讲台,但无声的爱却滋润着整个南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