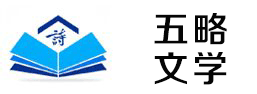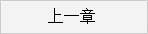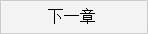老太太就是我了——年逾古稀,不谓不老吧;一头亮爽爽的白发更成了醒目的告示。三轮车夫(更准确的应称“全封闭载客三轮摩托车司机”)呢——纯属巧遇,该算是缘分了。
这事还得从小金鱼说起。
前天晚上暴雨骤降,院子里的小水池一夜溢满,几条小金鱼眼看要游出去了!于是我赶紧放水:起码得减少两寸吧。
但,不想却忘了关排水阀。到次日下午才猛然想起。走近一看:干干的池底上五条红红的小鱼全都“躺平”了,几只绿头苍蝇正在嗡嗡营营呢!
唉,别提我有多懊悔了。自打小金鱼进驻我家,算来已有四五个月了。从孩子们刚买来时的一二十条,到现在就剩五条了。也算是适者生存吧,数日来这五条一直活得很好,而且总是集体行动,两条大的常玩“追鱼”:红的一条紧追花的一条,飞快地转来转去;其它三条也尾随其后,像在助战一样。小小的鱼群为小院增添了勃勃生机,池中的睡莲都显得分外娇艳,“一、二、三、四、五”七岁的小孙孙更是蹦蹦跳跳地数来数去。
但,这下可好了!咋向孩子们交代?怎么说得过去?唉,附近又没有卖金鱼的。小区门口的小超市倒是有活鱼,但只有草鱼、鲫鱼、乌鱼……而且都挺大——最小的也有三两多重。咋办?不如先买两条试试。于是我买回两条小鲫鱼。
重新放满池水,赶紧将两条鱼放入。虽然有一条“打偏偏了”,但另一条游得甚好。
午饭前放入水中,下午竟都自在地游动起来。第二天早上也都游得挺好。但,没想到的是:傍晚再去看,两条鱼都翻白了,而且一动不动——显然是死了!我只好心痛地拾起,打整打整放入冰箱。
唉,偏偏这天又是周日,晚饭后孩子们照例又都过来了。小孙孙一进门就高声嚷嚷:“奶奶,小鱼喂了吗?”小家伙最喜欢喂鱼了。可现在,唉,怎么说呢?虽然谁也没有责怪,但显然都挺惋惜的——好不容易活过来的五条,刚刚适应了环境……
唉,咋弥补呢?我盘来算去:再买小鲫鱼吧,兴许这四平米的小水池就养活不了那样的鱼;但金鱼,可又上哪儿去弄呢?想了一宿——连做梦都在买鱼。
第二天清早,一睁开眼,忽然闪过一念——“上网!”嗨,咋把这茬忘了!我霍地坐起,打开手机。果然查到本街区内就有几处售卖金鱼(观赏鱼)的。其中最靠谱的是“水族生活馆”,而且留有联系电话。打通以后,说是就在江浦路西站,乘28路公交车便可直达。
早饭后我便背上双肩包,装入两个大塑料瓶,兴冲冲地出发了。
但,小区门口的公交站并没有28路车!
候车处坐着一老一少两位男士。见我走过去,那位穿“交投”工作服的小伙子,大约三四十岁吧,便站起来让座。但他们都不知道28路车。再问“江浦路西站”,也都是一脸茫然。看我挺着急的,小伙子便上下打量着我。我也下意识的看看自己:浅蓝色的碎花连衣裙,黑色的平底凉鞋,亮爽爽的齐耳超短发——洁白如雪,毫无杂色;口罩也带得好好的呀。
“可以问一下您的年纪吗?”他略带歉意地问。
“哦,七八十岁了。”我笑道。
“我帮您查查看吧。”他马上掏出手机,直接用语音进行查询。结果是:到前面的地铁站乘40路公交车,然后再转乘……。此时站上又来了一位年轻女士,小伙子又向她询问,果然得到了证实。
看来必须转车了。这对我来说倒是家常便饭:兜里揣着“老年乘车卡”,咋转都行;但,前面的地铁站必须步行两站后才能到。我不由踌躇起来:天空一片瓦蓝,大街尤显宽阔,街心那一排紫荆花更红得亮眼——今天是“35度、晴”——出门前我就查过。看我挺为难的,小伙子便说:“叫辆三轮过去吧——喏,街对面就停着一辆,红红的。”是啊,这倒不失为一招。我连忙点头,“喂,三轮——三轮——”他便扬起手臂大声招呼,那辆停在树荫下的机动三轮果然掉转车头,横过街来。
蹬(开)三轮的是一位五十开外的男士(就称他“大叔”吧)。这位大叔胡子拉碴的:口罩吊在下巴底下,露出红红的鼻头。他眨巴着布满红丝的眼睛问:“到地铁站吗?五元钱。”再问他江浦路西站呢?说是不大清楚,但晓得是朝哪个方向。
“边走边问嘛,保证把你送得到。”他说。
我想,反正就在本街区内,也不会远到哪去。与其转几次公交车不如就坐他的三轮直达吧。
“那,车费呢?”我问。
“总得有十几块钱,就算十五元吧。”他说。
于是我上了他的车。
好多年没坐三轮了。这简单的二人座倒也是沙发垫,只是,一坐下才觉得很热——阳光斜射到脚上,那薄薄的车皮怎能档住末伏的酷暑呢。
“啊,大热天蹬三轮,也真够受的。”我说。
“成都还算好哟,重庆才叫热得恼火。那里没得这种三轮,全是靠棒棒挑。”
咦,他怎么这么熟悉?“你在重庆干过吗?”我不由脱口而出。
“是嘛,才出来找活路那几年,就是在重庆当棒棒。”他回答得倒挺爽快。我一下想起了热播过的方言电视剧《山城棒棒军》:是啊,顶着四十度的高温,挑着百十斤的担子,一步步登那陡峭的梯坎——怎么受得了啊!我不由对这位“复员军人”肃然起敬。
“哎,你把车门都打开就凉快了嘛。”他说着帮我把车门全部拉开。但,我又拉回一大半——这小小的车厢,开着门多危险!宁可热点,安全要紧。
这位大叔开车挺谨慎的:每到十字路口,即便大路上就他这一辆车,也会主动停下来,并盯着红绿灯对我说:“还是开慢点,安全些……”。而且也的确是在“边问边走”:遇到路边停着这种红色三轮他就靠过去问路,对方倒也都耐心地指点着。
“前面路口倒右拐,不要过桥,直走就是江浦路了。”最后一位指路的三轮车司机说。于是大叔便不再左顾右盼,一直向前驶去。
果然看到了公交28路站牌。我便注意起街边的商铺,没多远就发现了《水族生活馆》的牌匾。于是车就在路边停下了。
“这样吧:我还坐你的车回去,来回一起付费,行吗?”
“三十元啰。”他立马回答。
“呃,往返一起算……”
“那就少两元嘛。”
“二十八元?”
“对头。”
“好的。你就在这儿等我吧。是先付钱,还是?”
“等你回来嘛。”
于是我下了三轮,走进水族馆。
虽然门面不大,但里面却挺宽敞。大大小小的各式水箱,五颜六色的各种金鱼,光彩陆离,四壁生辉。馆内凉幽幽的,颇有“水底世界”之感。
我问柜台后那位姑娘:有没有“最好养活的”金鱼,小孩子养着玩的那种?
她便领我来到一处大水箱前。只见许多纺锤形的小金鱼在欢快地游动。“这是‘草金’,两元一条。是最好养活的冷水鱼了。”她说。这时那位司机大叔也进来了。
我要了二十条,她便用一个小抄网捞起鱼来。“一、二、三……二十。”姑娘点完数后,大叔又加了一句:“再奖励一条嘛。”
她会意地笑了,于是又加了一条。
我指着旁边的鱼缸问:“这些大一点的呢?”
她说:“这叫蝶尾,五元一条。也好养”。
“喔唷,硬是好看!鼓眼睛,大尾巴!”大叔眼睛发亮:“喏、喏-——这条,这条。”显然他已看好了。于是我又要了一红一黑两条“蝶尾”。
看看我带的塑料瓶,姑娘摇摇头:“这个不好冲氧,还是用塑料袋吧。”哦,原来还需要冲氧!于是她用充氧机连水带鱼把大大的塑料袋冲得鼓鼓的。
“啊,起码有五六斤吧!”我盯着大叔看:“这……”
“我帮你提嘛,老人家。”他马上心领神会地说。
呵呵,“老人家”——我的这一头亮爽爽的白发常会赢来这样的尊称。我自是欣然同意了。
上车后,他把鱼提进了驾驶室:“挂到这里稳当些。”他说。的确——这连水带鱼的一大袋,只有挂在他的车把上才最合适。
于是我们开始返程了。
一路上随便聊聊。得知他家在资阳。我便说“就在铁路边上吧,交通挺方便的。”
他道;“我们是在农村,在很里头,只有一条泥巴路,还是不好走。”问到农村的情况,他说:“年轻人尽都出去打工了,只有老人还守到屋头。”
“那些地呢,都撂荒了吗?”我问。
“唉,荒得多哟,草都长起好高——没得法呀——种庄稼根本挣不到钱,搞不好还要倒贴。出来打工么,总还能挣几个,给留在屋头的老人改善一下。”
我默然了。看看他那件陈旧的蓝色纤维短袖:背后的下摆处还有一个明显的破洞;再看看他的头发:虽不至像一堆蓬草,但显然是好久没理了。唉,这位大叔,日子过得也挺不容易的。
路过一个挺气派的小区。只见大门右侧,街边上停着两辆三轮板车,一辆堆满水果,一辆摊放着蔬菜。于是我灵机一动:现在也有十一、二点了,回家再上超市……不如就在这儿随便买点吧!征得他的同意,车便停在了一棵葱郁的大榕树下。见他已跳下车了,望望车门外火辣辣的太阳,我想:不就是豇豆、苦瓜嘛,就托他帮忙各买两斤吧。“要得。”他爽快地回答,径直向车摊走去。我也就索性坐等回音了。
只见他在那儿认真地挑来选去,还看着秤杆讨价还价。
“一共十元,我砍成了九元。”他兴冲冲地报告。我付了款,又托他再帮我买一个小西瓜。
“无籽西瓜,三元钱一斤。这一个是十八元,我帮你要成了十七元——嘿嘿,又省了一元。”大叔又乐呵呵地报告,就像是给自家买了便宜货一样。
我也挺高兴,倒不在省下了两元钱。我之所以敢买这么多,其实已经打好了主意:请他帮忙送到家里——从小区大门口到我家还有四五百米远呢。我把想法告诉他:“……那就加两元钱-——凑个整数,三十元,行吗?”他盯着我,爽快地回答:“要得。唉,你们老年人,出趟门不容易哟。”
我心中霍然一震:如此爽快!显然不是因为那追加的两元钱;而是——“老年人”。尽管被尊称为“老年人”并不顺耳,但我这一头亮爽爽的白发显然触动了他,或许使他想起了远在农村留守的白发老母亲……。
车停到了小区门前的广场上。我告诉他;“不用担心,你只要带好口罩紧跟着我走就行。进门后要测体温的——照我的做就可以了。”进大门后,他还是主动去向门卫解释“我帮她拿东西……”其实门卫倒并没在意。测体温时,他拿手机靠上测温口,呵呵——等于没测。好在也没人注意到。
“哦,这里头好寛呀。”他四下打量着,“好荫凉哟!我从来没进来过!”受他的感染,我也不由对自己的小区再次刮目相看。的确,我们小区的绿化确实不错——我的一首配图小诗《小区即景》就曾获得网友们的频频点赞:
仲夏丽日,满目翠碧。
草木葳蕤,宛若园林。
步道广场,一处一景。
开窗见绿,出门踏青。
浓荫蔽日,鸟语蝉鸣。
我不由佩服起他的眼力,对他又多了一份好感。
“哎,豇豆呢?”他忽然停住脚步,看看左手提的鱼,右手提的西瓜,诧异地问我。
“哦”我说:“西瓜和鱼就够你拿的了,豇豆和苦瓜我都放到双肩包里了,你看,喏,我背着呢。”
“哦。”他这才放下心来。
进了单元门,上了电梯,到了我家门口。我刷开门锁,掏出三十元钱递给他(来回的车费加两元辛苦费):“谢谢你了”我说。
“哎,谢啥子哟。”他放下手中的袋子,乐呵呵地接过钱,便转身要走了。
“等一等。”我赶紧走进屋,打开冰箱,取出一瓶可乐递给他:“天太热了,你也凉快一下吧。”
“这……不、不。”他忽然局促起来。
“这一路辛苦你了,解解渴吧。”我说。
“哦——”他盯着我的眼睛,顿了顿,才伸出双手接住:“谢谢你啊!”声音有些哽咽,眼里闪动着泪光。
“哎,快别说了,是我该谢谢你啊!”我不由甚感愧疚——这一路的真诚相助,那区区的两元钱……
望着他的背影,我忽然想起大山里的乡民——想起了自己二十年前的一篇旧作《那年、那山、那人》。当年,作为国防三线厂的员工,在那出门就爬坡的偏远山乡,每逢赶场,我们便常常请乡民代劳:把向他门买的东西(粮食、瓜果等)帮我们送(背)到家中。从集市到我住的那片宿舍,要爬一个高约二百级左右的坡;而他们也总是毫无怨言,心甘情愿地背着背篼爬坡上坎,无偿地为我们代劳。
啊,那一个个难忘的身影,那一位位善良的乡民……眼前这位大叔不也和他们一样吗——虽然进了城,成了打工一族,其淳朴善良,助人为乐的秉性依旧一如既往。而大叔的一次次尊称更令我感怀:“老人家、老年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尽管时代在变,但延续了数千年的传统美德依然存在,尊老敬老已成为融入国人血脉中的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