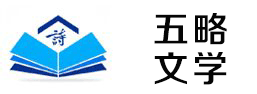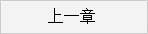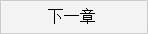黯淡了的、远去的,也是最那一忘怀的。
岁月啊,你永远带不走那一串串刻骨铭心的记忆!
谨以此篇献给我的父亲,一位平凡的老农垦人。
献给与他同时代的农垦前辈们
-------作者
求学生涯
1937年农历腊月初八,在黑龙江省明水县的一个小村庄,在北方凛冽的风雪中,一个男婴降临在一栋摇摇欲坠的茅屋中。他,就是我的父亲马景志。
1994年4月,父亲告别了近40年的农垦工作岗位,退休于内蒙古自治区,大兴安岭农场管理局,东方红农场场长任上,回家过着半休闲半经商的生活。
听父亲讲,我家从祖上开始,一直是从事农耕,在解放前,过着身无御寒衣,家无隔夜粮的生活,在饥寒交迫中挣扎,受尽了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
祖父16岁与祖母结婚,15岁给地主扛活打工,因为有一手好农活,财主便让祖父当打头的(领工)。常年超负荷的劳作,使祖父患上了哮喘病,再也干不了农活。三十几岁的人一干重活便吐血。就这样,靠着多年的积累,挣了十几亩地,祖父母把一切的希望寄托在这点土地上,他们起早贪黑的劳作,冬天没有棉衣穿,祖父便把棉被围在身上御寒,祖母一年四季一身单衣,冬天打场,手脚都冻成炎疮,一年到头除了交日本鬼子的荷粮(所谓的余粮),家中所剩无几了,过着半年粗粮半年糠的饥迫生活。
1945年,那年父亲9岁,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解放了父亲的家乡,打土豪分田地,父亲家的日子也好过些了。祖父母想到过去所受不识字的害处,决意让儿子成为一名有文化的人,父亲也自小儿就有一个梦想,将来做一个有知识的人,用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用知识帮助别人。当年冬天找了一位先生,父亲就这样上了一年私塾。
1949年,农村成立了小学,祖父母送父亲到2公里的树仁小学上学,因父亲读过私塾,老师让父亲直接跳入二年级。
这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一天,父亲和全国人民一样,穿上了新衣裳,学校挂起了五星红旗,全校开庆祝会,老师非常动情的对大家说:“同学们,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终于当家做主了。”接着老师便教他们自己编写校歌:“吾学舍万户向中央,百年树仁颂家乡.............”
1954年,父亲小学毕业后,因学习成绩优秀,被保送到明水县城上初中,接着父亲经过三年的学习后被国家保送到齐齐哈尔市农校上学。
从1949年到1959年,父亲十年的求学生涯中,是在极度苦困和艰难中度过的,也正是这十年的风雨坎坷的磨砺,使父亲从一个不识只无的穷孩子成长为一名有知识,有道德,有坚强意志的新中国一代知识青年。
父亲在他的回忆录里对他十年的求学生涯总结中说:“如果没有父亲及亲朋的支持,如果没有共产党的培养,如果我没有坚强的毅力,也不会有我的今天。十年的求学生涯,让我倍尝生活的艰辛。懂得了人生只有靠自己不屈的努力,便有渴望成为一名对社会有用的人,对后代子孙负责的人。”
时至今天,父亲永远不会忘记1946年的冬季,为了攒点学费,他为一家姓郭的放牛,一次一头牛掉进了冰眼里淹死了,姓郭的地主不但扣下了父亲一年的工钱,还放出十几条大狗咬伤了父亲,因没钱医治,东家又不管,祖母每天用烟袋油子为父亲抹伤口,也许是穷人家的孩子抗磕打,不起眼的烟袋油子救了父亲一命。
读小学时,父亲实际是在半工半读中度过的。因为祖父常年卧病在床,家里的农活只有靠祖母和父亲承担,父亲利用早、中、晚等课余时间帮祖母干农活,上午和下午上学读书。
这期间,父亲的家庭经济条件非常拮据,交不起学费,学校可以免收,父亲自己也非常节俭,一支铅笔用的拿不住了,祖父便做一个铁皮筒接上用,笔记本用黄钱纸(祭祀用的黄纸)自己订的,用完正面用反面。
父亲有一位叫张俭的舅舅,靠做皮活为生,他时常接济父亲读书。一次,他见父亲的腰带是根草绳,便把自己的皮带送给父亲,时至今日,父亲仍就扎着这条皮带,算起来已经60多年了,皮带中间已经断成了两截,父亲几次都用手线缝上再用,一次我给他买了根新的,他说:我不用,我现在的这条腰带是你舅爷给我的纪念品,我死后也要戴在身上。每当我看到父亲的皮带,心里总有一种酸楚的感觉。
繁重的劳作和学习生活,极度困苦的生活条件,对一个年仅十来岁的少年来说那种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了。但这一切并没有使父亲退缩,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要做一个有知识的人,要用最好的成绩报答父母及亲朋的厚望,报答党的培养。也正是这种信念的驱使,父亲以全校第一名的学习成绩,不经任何考试被学校保送到县中学上学。
中学生活对已家徒四壁的父亲来说更加困难了。
1954年的冬天,是父亲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候,父亲被保送到县中学上初中,并享受二级助学金待遇。
开学前,祖母把两床棉被并成一床,让父亲上学时半铺半盖。父亲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开学那天。临离家时,祖母含着眼泪叮嘱父亲要好好学习,别辜负了老师及家人的培养。当父亲坐着祖父赶着的爬犁走到很远的地方时,他还能看见身穿单衣的祖母在瑟瑟的寒风中久久伫立的身影。
在县中学临分手时,祖父给了父亲五元钱,这点钱,领书和买学生用品后,所剩无几了。父亲便向一位亲戚借了十元钱才得以度过开学后的第一个月。第二个月开始,学校的助学金发下来了,也只有每月五元钱,只够半月生活费用,虽然当时物价很低,但每月五元钱也无法解决了全月的生计。
为了解决下半月的生活费用,经老师批准,父亲每月中旬利用星期六大扫除的时间回家取粮食到校换粮票。学校离家约25公里,父亲每天下午5点钟出发,半夜十二点到家。那时人家少,十里八里见不到村庄,夜里又常有野兽出没,一个14岁的孩子,夜间一人走路,甭提该有多害怕了。半夜到家睡半宿,第二天早上返校,家中没有盛粮的口袋,祖母便把她的一条破单裤补了又补,扎紧两条裤腿,里面装上粮食,再把裤腰扎好,父亲把它往脖上一搭,再走25公里返校。
三年的中学生活,使父亲过早懂得了人生。他在回忆录中写到:“这种艰苦的磨练,使我进一步懂得了人生岁月的不易,促使我学习更加努力。”
1957年初,父亲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他初中的学业,并被保送到齐齐哈尔市农校上学。
中等专业学校学期为三年,这三年,父亲在他回忆录中感慨的说道:“是在风云变幻,动荡不安,转战南北中度过的。”
三年间,他经历了“三反”、“五反”、“大鸣大放”、“大辩论”、“大跃进”等政治运动。参加了1957年夏季松花江防洪会战和勃利县筑路工程。
当时,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学生每月只有十二斤粮票,吃的全是菜根加菜叶的代食品。
三年间,学校又经历了几次合并,父亲在1959年毕业并被分配到黑龙江省农科院园艺研究所工作。
三年的农校生活,父亲结识了一位叫方志义的同学,他比父亲大两岁,是学生会主席,父亲是学习委员。见父亲生活困难,他便时常周济父亲,三年间从未间断过。二人同在一个班级,住一张床,吃一碗饭,又分配在同一单位工作。直到1961年父亲下放到黑龙江省克山农场支边后才分开。随着时间的推移,二人的感情越来越深,情同手足,心心相印。就是分开后也从未间断过来往。每次方伯父来我家串门,父亲总是盛情款待,毕恭毕敬。每次两人都秉烛夜谈到天亮。1993年方伯父因病故于哈尔滨,临终前,他拉着父亲的手,指着他们过去的照片,两人都哽咽了。方伯父故后,父亲每年都要到哈尔滨祭奠,烧上几张纸,共同喝上几杯酒,诉述衷肠,以慰隔世思念。
投身农垦
1959年11月份,父亲与几名同学被分配到黑龙江农科院园艺研究所工作,直到1961年下放到克山农场支边,两年的专业科研工作,进一步丰富了父亲的专业知识,为今后的事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也就在分配工作后的第二年,父亲与母亲完婚。
我的母亲叫李淑芹,结婚那年20岁,是祖父母在老家给定的。我母亲美丽、贤惠、勤劳、孝顺、有知识,可以说具备了中华民族所有的传统美德。在我的记忆中,她从没和家人或邻里红过脸,也从没对儿女动过一个手指头,父亲脾气不好,常和母亲动怒,可每次都被母亲的沉默和温和所平息,长期困苦生活的折磨,使母亲过早的患上了关节炎,30岁的时候,双腿因疼痛变型,现在走起路来还一跛一跛的。
祖父去世的早,祖母又没生活能力,我的两个姑妈和一个叔父都是在我父母的抚养下长大成人的。叔父临终前曾是一位军官,大姑妈曾是一位小学教师(现已故世),小姑妈是位医生,他们常对我说,他们能有今天多亏了哥嫂的抚养。每到节日,远在他乡的姑妈和叔父总会给他们的哥嫂送来一份问候和祝福,每每此时,母亲总会躲在无人的地方独自饮泪。
1962年11月份,父亲带着全家来到了黑龙江省克山农场,投身到火热的中国农垦开发建设中,从此,父亲便把自己的后半生无私的献给了中国农垦这片沃土,献给他苦苦追求的中国大农垦梦。
父亲在克山农场工作了18年,18年的克农生活,父亲是在政治风云变幻中,在生活、工作极度困难中度过的。正是历次的政治运动和那种艰苦创业的经历的磨砺,使父亲逐步成长为一名有着丰富的生活阅历和工作能力的中层干部,成为一名具有高度责任感,清正廉洁,刚直不阿,勇于奉献的共产党员。
那时,全国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其间,生活极度困苦,家里没有吃的,祖母便每天拣雪地里的黄豆回家磨豆腐吃,全家每天吃少量的粗粮和豆腐糊口。
父亲在“四清”运动期间,一次到外地出差,饿昏在车上,若不是车上的同事们抢救,父亲绝无今天。
最使我难忘的是父亲在文革期间的经历,文革初,父亲在克山农场5分场32队当队长,一次为接待鸡西市的下乡知青,半宿没回家,赶巧的是母亲在那天晚上生下了我的小妹妹。当时,母亲难产且大出血,若不是抢救及时,母亲绝无生还的可能。那晚,祖母到队里找了父亲几次,父亲都因工作太忙而没有回家,大约早上一点多钟回来,听过祖母的诉说,他独自在母亲床前待了一整天。现在每每提到此事,父亲还常常自责。
后来,父亲被造反派打成了“走资派”,白天干活,晚上挨批斗,我至今还记得,每天早上,父亲与其他几位走资派,都要站在队部宣传栏前,向毛主席请罪,并背诵毛主席语录:“革命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力,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活动。”“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革命到底。”我每天都去看父亲的请罪,这些语录,到现在我还能倒背如流。
父亲被打成走资派后,被关在小学仓库里,家里的生活只有靠母亲支撑,造反派根本不管你家死活,因家里没有取暖的煤,每天早上我都要与另外几个和我同命运的孩子去拣煤核,以供家里取暖。尽管如此,也解决不了御寒之用。每天晚睡前,母亲都要从地窖里拿出一盆土豆,放在炕上最暖的地方,以备明天食用。
那时,我已上小学一年级,同学们都当上了红小兵,每天给走资派游街,开批斗会,而我因父亲的原因,学校拒绝我当红小兵的要求,因我属黑五类的子女,每天上学都要站着听课,并接受红小兵的监督改造。后来,一个造反派头头告诉我,只要你跟父亲划清界限,便可当红小兵并可坐着听课。一次放学后,我利用给父亲送饭的机会,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父亲听后默默地看着我,我分明看到了他眼里闪动的泪花,他用伸出铁栏的双手,抚摸着我头说:“儿子,你恨爸爸吗?”我默默的摇摇头。他又说:“只要你心里有爸爸,只要你能当上红小兵,你就答应他们的要求。”我听后,点一下头转身走了,走出很远我回头望去,父亲仍站在铁窗前呆呆的看着我。时至今日,我仍然记得那刻骨铭心的一幕:残阳如血,寒风凛冽,飞雪肆虐,一位父亲站在铁窗后目送着远去的幼小无知的儿子······
当时父亲的这番话,在我心中没有产生多大的反响,后来我长大了,渐渐地明白了父亲的一片苦心。现在每当我想起这番铁窗对话,心中总是隐隐作痛。
就这样,我如愿以偿的戴上了红袖标,当上了红小兵,再也不用站着听课了,也可以和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了。
还有一件事,也发生在父亲铁窗岁月时,它让我永远无法忘却。
记得那时1969年的元旦,我家的一位好朋友在元旦前一天的半夜,偷偷地送来了半盆红烧猪肉。第二天午饭时,母亲装了半饭盒让我给父亲送去。当我来到父亲被关押的仓库时,一名站岗的造反派要检查,当他看到里面的肉时,怪声怪气的说道:“走资派有什么资格吃红烧肉?只有造反派才能享用这好吃的。”说着便伸手来抢,我紧紧的抱住饭盒不放,就这样我们疯狂的撕抢着,父亲在铁窗后大声喊着:“儿子,给他吧!”我仍死死的抱住饭盒不放。气急败坏的造反派拿起身边的一个木棍,恶狠狠地向我的右脚打下去,瞬间,我只觉得一阵钻心的疼痛,一下瘫倒在地上。我的脚被打断了!看到这些,父亲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一脚踹开紧锁的房门,抱起我向家奔去。因为情况特殊,造反派给父亲两天假。当晚,父亲请来了一位正在劳动改造的老中医,给我接上了伤脚。
三个月后,我的脚却出现了异常,每当试着行走时,伤脚就脚跟朝里,脚尖朝外。看到这种情况,家人十分着急。也许是天不毁我,因为我叔父是一名解放军干部的原因,父亲被“解放”回家。他便请来了另一位老正骨中医,把我的脚在原伤处打断后再重新接上。谢天谢地我总算没残废,不过每当阴天下雨,右脚总有一种难忍的酸痛感。现在我还时常想,当时打我的造反派如今还健在吗?他还是否记得此事了,他若是想起此事该做何感想?
十年动乱不仅给我的身体造成伤害,更在我的心里刻下了深深地烙印,也让我过早的认识了社会,逐渐的读懂了人生。
父亲在回忆这段动乱的岁月时说:“十年文革,不仅祸国殃民,对个人来说,受点委屈和冤枉不算什么,更主要的是我的大好时光在动乱中白白的逝去了。”
父亲被解放后分别担任了农场五分场副场长、农场科研站长和农场农林科长职务。
1978年,父亲离开了他辛勤工作了18年的克山农场,被组织上调入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农场管理局诺敏河农场工作。
转战大垦区
十年的动乱结束后的1978年7月1日,父亲离开了他生活18年的克山农场,和我一同调入大兴安岭农场管理局诺敏河农场。父亲任生产科长,我当上了一名电工。
诺敏河农场是1977年开发建设的,父亲调入后还担任了农场开荒副总指挥,场长任总指挥。那时父亲带人在野外开荒,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蚊子、瞎蒙、小咬早、中、晚三班倒,叮的人脸上红肿流血。夜班开荒更可怕,车在前行后面野兽跟着跑,还时常翻车打误,一干就是一夜。生活就更加艰苦了,住帐篷冬冷夏热,令人难熬。吃的是黑面馒头土豆清汤,时不时的还会从汤里捞出几只死老鼠。
艰苦的工作也使父亲经历了几次生与死的考验。
他永远不会忘记1981年的那个黑色星期六。他随同一位副场长及两名技术人员乘车到六队检查麦收工作,在回家的途中,大约晚九点多钟时车行到1队和2队中间的诺敏河岸边,一不小心人车掉进河里,人在车里坐着,水很快的漫过了肩头,他们急忙打碎了车窗爬到车顶。由于水流湍急,车不停的往下自行滑动,眼看着水很快的就要没过膝部,他们又都不会水,只好喊人求援。大约过了半小时,1、2队的队长听到了喊声,马上发动了拖拉机到河边救人,两台车在两岸同时下水,行不远被水淹灭了,这时水已过腰了,正在这危急时刻,2队长刘常胜找来一只小船,才把他们就出来,从此他再也不敢夜间过河了。
艰苦的生活,繁重的劳作,无情的摧残着父亲的身体。
1984年初冬,父亲常常感到食道疼痛,还常伴有心痛。当时,他自己怀疑是食道癌,但因工作太忙,又怕家人担心,一直瞒着大伙坚持上班,眼看着父亲的身体一天天消瘦,我们心急如焚,劝他到哈尔滨去治疗,可怎么劝他也没用。春节过后,父亲才在母亲的陪伴下去哈尔滨做了检查,结果是患了肠上皮生化。当时大夫叮嘱父亲要回家保养,半年后再上班,可回家后,父亲第二天便上班了。
父亲因患病吃不下饭,每顿只吃一小块馒头和半碗奶粉,望着父亲逐渐消瘦的身体,我多次劝他住院治疗,可每次他都说忙完这段工作再说。就这样一直坚持到当年六月份,父亲又患上了心绞病,每天早上都有疼一阵,每次都疼得他翻身打滚,呻吟不止。当时也不知是心脏的毛病,每次都注射一针阿托品止疼再上班。不久,父亲因过量注射阿托品中毒险些丧命。还记得那是一个早上,我陪父亲乘车到大杨树镇给他检查身体,当车行到宜里农场6队时,他的病发作了,瞳孔扩大,口无只言,处于半昏迷状态,我和司机忙驾车拉着父亲来到宜里农场医院抢救。此时,父亲已完全处于昏迷状态,我急忙和家里取得联系,场长带着有关人员拿了8000元钱,把父亲送到大杨树镇农场管理局医院抢救,经过一昼夜的抢救,父亲终于转危为安。也许真的是祸不单行,当年父亲又患上了肺结核。于是父亲在我的陪伴下再次到哈尔滨治病。三个月后才康复出院。
回忆往事,父亲深有感触的说:“当时多亏场领导和组织上的关怀,我才有今天,要不然,我十个马景志也都完了。”
1984年父亲离开了工作6年的诺敏河,在副场长任上被组织上调入扎赉河农场任生产副场长。1992年父亲被任命为东方红农场场长。第二年10月,父亲因患脑血栓住院治疗。出院后,组织上批准了父亲提前退休的请求。那年父亲56岁。
纵观父亲的大半生,他把工作当做生命,几乎投入了全部的精力,恪尽职守,廉洁办公。在东方红农场任场长期间,白天操劳了一天,晚上还要边输液边接待来家中谈工作的同志们。我们劝他休息几天,他说:“看我的身体还要几年干头,我要站好最后一班岗,让群众信服,不让组织上失望。”
忘我的工作和无私的奔波,使父亲早已病残的身体再也承受不了工作的辛劳和压力。1993年十月父亲因患脑血栓住院治疗。住院期间,他便萌生了退休的想法,他对我说:“就凭我这身体,就是上班还能干什么?咱绝不干那种站着茅坑不拉屎的事儿,把担子交给年轻人,于公于私都是好事。”我问他,“你退下来,遗憾吗?”他沉默了一会儿后对我说:“我这一生啊,就是在追求一个个梦想。小时候,我的梦想就是进学堂当一名学生,后来,我的梦想就是能考进大学,做一个有大学问的人,这样,即可以改变我的命运,还能为国家多做贡献。投身农垦后,我的梦想是靠自身的努力当一名农场场长,带领职工群众用我所学的知识改变农垦贫穷落后的面貌,建设中国的大农垦、现代化农垦。退休后,我要办一家农贸服务部,为农垦的发展发挥余热。对此,我不遗憾。我唯一的遗憾是没到退休年龄就下来了,要是我身体允许我在干上几年多好啊。”
听到父亲的一番话,我若有所思,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时代都会有不同的梦想,这些梦想不是孤立的,脱离实际的,它们与时代紧密相连,与时代共同脉动。千万个梦想汇集在一起,就是一个强国富民的中国梦!
退休后,父亲卖掉了东方红农场的住房。向亲友借了一些钱,在大杨树镇买了一栋临街房,办起了一家农贸服务部。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今后有生之年,只要身体允许,坚持干活(办农技服务部),我在几十年的工作期间,没给儿女留下什么家业,现在我要利用退休在家的时间为他们挣点钱,让他们不再像我年轻时那样苦。退休后我每天坚持体育锻炼,还常吃药,争取多活几年,哪怕是一年也是宝贵的!”
风烛残年的父亲,把自己大半生的好时光贡献给了农垦这片沃土,献给了他苦苦追求的梦想。无怨无悔的工作了几十年,到了晚年还要为儿女的幸福操劳,写到此处,我不禁想起方冰的《老树》:连最后几片叶子/也要落尽/老树/以铁一般的树干/撑起了晴空/又开始了春的梦…… ” 爸爸呀,我敬爱的父亲,你永远是儿子心中一棵永不凋落的苍松,一座不朽的丰碑!
这就是我的父亲,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一名平凡而又伟大的追梦者;一名把毕生精力无私奉献给中国农垦事业的农垦人!
(完)
2013年5月20日夜初稿
2013年6月25日夜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