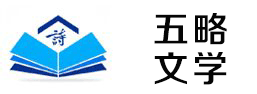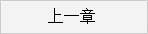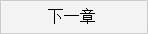新诗技巧十二讲
翟大炳
一、再现与“预成图式”
诗歌创作源泉只能是社会生活,离开了社会生活只能是无源之水,因而读者便可以从诗歌中看到时代的投影,它就是人们所说的再现功能。但这种再现决非对生活的复制,所谓镜子式的反映现实生活并不确切,这是因为每个诗人由于经历、文化教养乃至性格的差异,即使面对同样的社会现实,他们的视点也是不相同的。如一首题为《爱情》的诗:
恬静,雁群飞过
荒芜的处女地
老树倒下了,嘎然一声
空中飘落着咸涩的雨
这不是现实生活中一幅深秋的画面吗?秋雨绵绵,大雁南飞,原始森林中一片寂静,它与现实生活中爱情有什么关系,既看不到少男少女们追逐嬉戏,更看不到他们之间在花前月下的相依相偎,为什么诗人偏偏从中看出了爱情,原来是诗人为他所理解的爱情找到了一个“客观对应物”,一幅象征的画面。那就是他看到了那种苦尽甘来的成熟爱情,此时的恋人是多么激动啊,他俩沉浸在幸福中。当人们高兴到极点时,哭是最好的表现形式,所谓乐极生悲,是“以哀景写乐,倍增其乐”。读者笔下的爱情是经过自己眼光过滤的选择,由此可见,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再现模式,人们的“视”是“知”所决定的,“知”就是“先有、先见、先把握”,通俗地说,就是人们在观察问题时,是由原先所具有的经验、知识所决定的。冈布里奇曾举出这样的一个事例:两个画家同时在英国德文特湖写生,一是中国画家蒋彝,一为英国画家,画成后却大不一样,显然是因两国画家文化背景不同所致。所以他说:画家“倾向于画他所愿意画的东西,而不是画他所看见的东西。”他认为这种原先就有的经验、知识便是“预成图式”,这“预成图式”制约了每个画家(诗人)的创作倾向。
如此说来,诗人似乎就不可能有创新的余地了,其实不然,因为这“预成图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应是一个开放空间,要不断予以更新,用他的话说,就是要时刻进行“修正”。“知”不应是一个凝固的经验与知识结构。他提出的创新公式便是“预成图式——修正”。他的上述主张确为诗人创作实践所证明。以女诗人梅绍静创作为例,她是北京下放知青,从大城市来到陕北延安后,其反差之大可想而知,那就是她认为延安太落后了。她将自己的感受写进自己的诗的初稿中。据诗人说,诗写好后便放下了。“也不知经过多少天,”她终于明白了原先的想法是错误的,看似落后的陕北农民,他们实在是无名英雄,历史是由他们所创造出来的,他们一不为名,二不为利,默默地贡献一切,这些人是中国真正的脊梁。诗人说,我写诗“并不是只写我自己的经历,跟我一起搓麻绳的女人,跟我一起背麦的人,跟我同睡一条大炕的女子,他们才是这诗真正的主人公。没有想到你只是一个短期来客,而它们才是这些日子的享有者,我敢说,开始写是不清楚的,是想自己比较多,但后来改的有了新含义,那含义就是农民的命运了。”诗人“开始想自己比较多”就是“预成图式”,而“后来改得有了新含义”,便是经“修正”后的创新,也就有了下面脍炙人口的,《日子是什么》:
日子是撒满泥土的小蒜和野葱儿/是根蘸着水搓好的麻绳/是四千个沉寂的黑夜/是驴驮上木桶中撞击水声/日子是雨天吱吱响着的杨木门轴/忽明忽暗地转动我疲惫的梦境/日子是一个会在嘴里止渴的青杏儿/这山塬上烈日下背麦人的剪影/日子是那密密的像伞似的树荫/正从我酸痛的胳膊上爬向地垅/日子是储存这清甜的水罐儿/正倒出汗水和泪水来哽塞我的喉咙
梅绍静对陕北农民看法的改变,可以说是她的新发现,这种“发现”恰恰是文学最重要、最实质、最核心的功能,“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
二、表现与表现性
如果说再现,是诗人的创作从外部寻找依据,那么表现则是诗人将注意力着重放在人们的情感世界,它是内宇宙——人们的主观天地。比起其它的文学样式,诗歌的重抒情性特征决定了它重表现。如蓝色的《圣诞节》:
总觉得塞进邮筒的信/对方不会收到/放在街旁的自行车会被人偷掉/总觉得端在手上的高压锅/马上就会爆炸/转播足球赛的电视机会出什么故障/如果撞上了什么东西/那一定会得脑振荡/如果这班车她还不到的话/我就要一个人被撇在世界上/一个成熟的男人/身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分量。
诗中主人公表现出来的心有余悸是一种卡夫卡式的焦虑,它是日常生活中人们常见到的。这是由于人生的种种困境常使自己愿望落空,或者飞来横祸始料不及。这样看,它似乎是一种再现,然而由于被极度夸张,重心已出现了倾斜,因为一个正常人不可能将这么多焦虑集中于一身,除非他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既然如此,诗人为何如此集中呢?显然,诗人是为了强化这种焦虑。
说起表现,常有一种“移情”的说法,即认为客观事物并不是有感情,是诗人将他的感情移到它们中间,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中的“花”和“鸟”,它们并没有感情,是诗人杜甫将自己的感情移给了它们。这见解虽有合理之处,但并不全面。格式塔心理学家认为并非所有客观事物都可以将感情移进去,还必须看到客观事物本身是否有表现性。如《诗经》中著名的送别诗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诗人为什么以杨柳来表现友人之间的送别时那种难舍难分的感情,并不仅仅是一种“移”,而是杨柳在风中那种特有的摆动就是一种表现性,格式塔心理学家称之为“力的式样”。阿恩海姆说:“就是那些不具意识的飘零的落叶,一汪泉水,甚至一条抽象的线……都和人体是有同样的表现性。”而人们的情感活动也同样是一种“力的式样”,当主客观“力的式样”处于大致相似时,也就有了共鸣,它也就是“异质同构”。徐志摩的《沙扬娜拉》中的少女羞怯状态为什么如此传神,原因也在次: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
那一声珍重里有甜蜜的忧愁——
沙扬娜拉。
诗中少女的羞怯表现与风中摇摆的水莲花“力的式样”如此的酷肖,没有上述酷肖,诗人的情感是移不进去的。
什么又是表现性呢?那就是诗人将情感表现反映在形式的突出位置上,以形式凸现诗人的情感。如贺海涛的《木材厂印象》:
雀鸟
在高高的圆木上
盘旋
电
锯
在
响
乍看,此诗不知所云,因它形式太怪了,可是当你在看此诗时,同时再读作者所写的附记:“八四年秋季的一个上午,我来到了北疆某个小城镇的郊外,在堆得高高的圆木上,电锯残酷地嘶叫着,我走开了,我想走进山林。于是便有了短短的《木材厂印象》。”此时便会豁然开朗,原来诗人是以具像的方式写出他对滥伐森林破坏生态平衡的痛心疾首:一棵孤零零的大树上只有两只小鸟凄厉地鸣叫着,怎能不叫人心碎。
从这首诗,人们不难看出,对它的欣赏,首先是从特殊的“形”开始的,你无法回避它。诗人试图把读者的注意力提升到语言文字的特征上,它突现出视觉因素,这样的视觉诗从形状上看犹如一幅画,与画不同之处在于不是用线条,而是用词的排列出一个物体的内在含义,目的在于激发读者把看到的东西更为诗意化。
三、诗歌的形式和形式感
长期以来,由于受到“内容决定形式”一元论的影响,形式的重要性被忽略了,似乎形式是内容的附庸。创作实践告诉了人们形式有独特价值,同样的内容,由于形式不同,其艺术效果就大不一样。形式往往最能体现出诗人的个性与他的独特发现,因它表现出作者选择了仅属于自己反映内容的组织构造。我们不妨先看看这一段文字:“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是奴隶。”然后再看下列: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
敌人用刺刀
杀死了我们
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
看
这是奴隶
经过比较,内容是一样的,但由于文字排列不同,前者被说成散文,后者被说成是诗,而且田间的这首诗被闻一多誉为抗战的“鼓点”,它就是诗人田间写于抗战时期的街头诗代表作《假使我们不去打仗》。为什么散文一经分行就有了诗意,结构主义诗歌理论家认为,首先它的可视的“形”被凸现了,它由此起到了端正读者“阅读态度”的暗示作用:即要求他们尽按照诗的程式,也就是用体现为诗的“文学性”去读它们。诗歌、小说、散文、戏剧都具有“文学性”,但他们的“文学性”又是不同的。所以,雅可布森特别强调地说:“文学科学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也就是使一部分作品成为文学的东西。”诗歌的“文学性”,首先是它的节律化特征,由于分行,“顿”的因素被凸现出来了,这种阶梯式的排列,“顿”处于加强状态,恰如闻一多所说:“如同一片沉着的鼓点,鼓舞你恨,鼓舞你活着。”结构主义理论家称它是一种“程式化的期待”。它显然是散文排列所不具有的。
什么是形式感?是指诗人感受形式创造的能力。由于形式是具有强化内容表达的作用,诗人对形式创造尤为重视,他们总希望将形式处于醒目的地位,也就是说,他写的诗不仅给你读的,也可以是看的“形”。如穆木天的《苍白的钟声》:
苍白 的钟声 哀腐的 朦胧
疏散 玲珑 荒凉 的谷中
—— 哀草 千重 万重——
听 永远的 荒唐的 古钟
听 千声 万声
……
诗人之所以采取词语间隔排列的“断行法”,是为了造成视觉与听觉融合的效果,这断断续续的排列与飘散的钟声多么相似。诗中的韵脚“胧”、“中”、“重”、“钟”的韵母“ong”就是对钟声的直接模拟,听觉得到了极其传神的体现。
当然,《苍白的钟声》并不仅仅是诗人以对钟声的模拟为目的,而是以引导读者透过它的背后作深入的现实联想,去感受当时的中国农村大地的颓败、落后与贫困。这种被大大扩张了的语言与联想义,是语言的音乐表现力与绘画表现力的完美结合,它使语言的“推理性”转化为艺术的“类比性”。由此,不难看出,作为语言艺术的诗歌,它的自然关系,即断断续续的诗句与生活的钟声同构,以及衍生出来的无穷联想义的相互作用,使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复合体,这不就是诗人与读者共同认定的形式感吗!
四、诗歌中意义和意思
诗歌中意义是指诗人通过诗歌内容所作的价值判断,这在放歌派的诗人中常见的是直截了当的方式。如郭小川的《秋歌》(之一):
秋天来了,大雁叫了;
晴空里的太阳更红、更娇了!
稻穗熟了,蝉声清了,
大地上的生活更甜了、更好了!
如果再看一首《路从峡谷通过》,其价值判断就不那么一目了然:
悬崖。中断的乐章。/风绝望了,把一串省略号/摔向深涧。/公羊,一只出色的领头羊/踏向最后一颗草芥,/默默地咀嚼着,而后仰起/长长的脸,象个瘦削的思想家。/它的整整一个纵队的家族停滞了,/母羊的眼泪流着悲哀,/乳头被卷毛的儿子咬出血。/山羊在另一个世界嘲笑着,/嘲笑这一群流浪者,/方队开始骚动……/只有高大的,有着一双仇恨/和/欲望的眸子的公羊,/又一次不甘心地选择。/终于,它认真地低下头。/把前蹄伸向风的深涧,/那山谷的底部……/交响乐,大提琴,号/骤然继续它的乐章。主题是一个勇敢的公羊赋予的。
如果从诗的表层看,诗人给我们展示的是由一只公羊率领的羊家族在崎岖山路上转移的画面,但诗人的真正的意图却不在此,因为诗人写的是他听美国作曲家格罗菲的《大峡谷组曲》之后的感受。美国亚利桑那州的科罗拉多大峡谷是世界上最为壮丽的自然景观,它原为印第安人居留地,然而由于白人的入侵,不得不被迫迁徙。由此看,这首诗的象征意义极为明显,它实际上写的是一支印第安人家族的大迁徙。如从这首诗写于1984年看,说它象征中国改革开放之举也无不可。也就是说,这首诗是多义的。语义学家认为意义有基本意义和附加意义两种形式,前者我们说它是意义,而后者的多义就是我们所认为的意思了。
诗歌的意义和意思,还可以从语言角度加以证明。语言学家索绪尔认为语言只是一种符号。作为符号,它是声音、形状与概念的统一。声音、形状称为能指,是书写形式,而它后面所含的概念称为所指,也就是它的意义,如同一枚钱币的两面,是不可分割的。通常的情况是一个能指对应一个所指,如“雁”,它读作“yan”,书写形式则为“雁”,它的概念则是一种候鸟。然而在诗歌中,能指和所指并不总是一对一的关系,它可以是一个能指,但所指却可以是两个,或更多,如舒婷诗歌中常见的“帆”“鸟”,在不同诗中就是有不同的所指。再看卞之琳的《断章》;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就一首诗而言,能指只能是一个,然而这首诗却因它的意义丰富而闻名。你可以认为它是一首情诗,两个相爱的人虽未见面,却以心心相印了。也可以说成是一首哲理诗,说明人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如果再换一个角度,它不正是一个失意人无比惆怅心态的折射吗?反之,一个人正春风得意,他眼中所看的这副风景是多么富于诗情画意:小桥流水,月白风清。虽然,这首诗是一个个能指排列,但在它后面却有那么多的所指。这不尽的所指就是我们所说的诗的意思。
为什么在一首诗中,有的是单一的意义,有的却是意思,这自然与诗人的生活境遇、文化修养有关。因而在欣赏中由联想与经验机制形成的价值判断体系也因此有了极大的差异,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地点的变迁,它还会不断衍生出新的意思。为庆祝卞之琳创作60周年,晏明在《世纪的桥》中说:
你依旧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依旧在楼上看你;/无边的静,倾听着你,/你又倾听,无边的静。//风景的桥,变幻的楼,/矗立于永恒的空间,永恒的宇宙,/明月从海上升起,滴着风的雨露,/装饰茫茫大海,淡淡哀愁。//在那遥远的千重门外,/你编织霓虹灯飘洒的古曲凄怆,/散步于草绿天涯的奇情异想,/又植根于梦于现实的土壤。//……站在遥远世界的桥头和楼上,/未来绝美的月色将装饰你心灵之窗。
这岂不是诗人在今天重读《断章》时,对它的意思又有新的发现吗!
诗人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平庸的诗人以自己的作品显示了自己的愚昧,优秀的诗人使读者看出生活中的愚昧,伟大的诗人使读者看见了愚昧的同时还能悟出它的根源:文化原型,它就是我们所说的意思。与意义不同的,意思可以有着本雅明所说的“震惊效果”。
五、诗歌中的习俗性规则
艾青有一首题为《给乌兰诺娃》的诗,开头有这么几句:
像云一样柔软,
像风一样轻,
比月亮更明亮,
比夜更宁静——
人体在太空更游行。
读后,人们都会为乌兰诺娃的优美芭蕾舞姿惊叹不已,多么生动的比喻啊!如果我们再看另一首题为《姑娘》的诗,虽只有两句:
颤动的虹
采集飞鸟的花翎
不禁感到茫然,虽然标题是明确的,但诗句中所说的“颤动的虹”与“采集飞鸟的花翎”究竟有什么联系?对前一首诗为什么一看就明白,人们会答道,它不是比喻吗。然而我们不禁要问,《姑娘》不也是比喻吗?我们认为虽然也是比,但它却有一个逐步扩展的过程。在诗人看,处于花季的少女是美丽的,但美到何种程度,诗人头脑中捕捉到第一印象便是挂在天边的颤动的彩虹,然而它分明又是诗人此时头脑中闪现出的种种飞鸟的羽毛,接着又有众多的羽毛编织出鲜艳夺目的花翎,实际上是一个意象叠加在另一个意象上。虽然这首诗的传达手段仍落实在“比”上,但它基本技巧便是意象叠加,而且是瞬间的印象复合。
作者与读者在交流过程中如同鉴定一次契约,只有双方获得认可才算在愉快的气氛中签约。能否签约,双方必须认同协议中的规则。由此,可以这样认为,诗歌中的技巧,实质上就是表现出诗人是如何将生活中的感受体现出来他所确立的规则。有的读者会问,为什么我们在读这些诗时并不感到有规则的存在,如《给乌兰诺娃》。其实读者早就在潜移默化认同规则“比”了,它早已千百次出现在读者脑海中了。自《诗经》以来,人们对“比”是太熟悉了,因此,它早已“内化”为自己认知诗歌常识的一部分了,也因此熟焉不察了。凡依据约定俗成规则所形成的诗歌技巧,我们称之为习俗性规则,只要不是拾人牙慧就可以写出优美的诗章。如公刘的《勐洞河上的七只天鹅》的比就富有创造性:
蛇一般冷轰轰的阴河/七七四十九道豁/悄没声息/溺毙于这深不可测/潭边钟乳铸的陡坡/栖息着倦舞的一群/白天鹅/白太鹅/白天鹅/白天鹅/白天鹅/白天鹅/白天鹅/七重无告的喑哑/七重幽冥的美丽/七重亘古的寂寞/天上地下/鬼魅们来此聚会/狂暴地/燃起了一堆/肉眼看不见的烽火/它们还顶礼膜拜呢/反反复复/唱一支我听不懂记不牢不可破学不会的歌
这首诗同样以“比”的方式写出了湘西宝靖县王村,即电影《芙蓉镇》拍摄地附近一溶洞瑰丽奇绝的自然景观。白天鹅是美的,但被残害了的白天鹅又是那样凄惨悲凉,它的含义是无法用一个美字所能界定。
约定俗成规则最大的弊病就是老调重谈而钝化读者的感觉,为克服这样的弊病,激活读者的欣赏兴趣,诗歌中的另一规则:设定性规则应运而生了。
六、诗歌中的习俗性规则
为什么要有设定性规则?现代信息论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每天接受到的信息量低于一定的界限,就感到极其难熬。因为人有一种基本倾向,即寻找刺激和时时改变刺激领域的倾向,通俗地说,即喜新厌旧。读者在读诗时也希望改变刺激领域以获取新的信息。因此诗人创作的职责就必须满足读者上述愿望,也就是说,诗人必须以新的技巧反映变动不居的生活来扩大读者的视野,满足他们的要求。那种旧瓶装新酒的方式总是捉襟见肘的,诗歌中的设定性规则也应运而生。这里不妨以艾青的《墙》与舒婷的《胡苏姆野味餐厅》作一对比。在《墙》中诗人说
一堵墙,像一把刀/把一个城市切成两片/一半在东方/一半在西方/墙有多高?/有多厚?/有多长?/再高再厚再长/也不可能比中国的长城/更高、更厚、更长/它又怎能阻挡/天上的云彩、风、雨和阳光?/又怎能阻挡/飞鸟的翅膀/和夜莺的歌唱?/又怎能阻挡流动的水和空气?/又怎能阻挡/千百人的/比风更自由的思想?/比土地更深厚的意志?/比时间更漫长的愿望。
这是一首好诗,它融入了诗人的哲学深思,使它意蕴深广。众所周知,由于柏林墙的存在,它将一个统一的德意志民族生硬地分开了。因此,这柏林墙就是专横、粗暴的代名词,它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舒婷的《胡苏姆野味餐厅》所表达的主题与《墙》基本上一致,同样是对柏林墙的谴责,然而读着下面的诗句,乍看有恍惚之感,但却为它新颖所吸引:
……墙上陈列着许多飞禽的标本
许多年来
鼓着翼
那些鸟儿
始终飞不出
这堵墙
那将自己隐于没于灯光的人
被灯光所惊骇
当他看见
多一个苦苦挣扎的姿势
在群鸟的悲鸣中
装饰墙
这首诗新在什么地方,依我们看来,诗人所使用的技巧比起《墙》来,它是全新的,是舒婷自己所设定的,而不是步艾青的后尘。这首诗体现出来的规则有三:其一是双重视角,即诗人和标本制造者“他”的两个不同的视角;其二是意象切割,作为飞禽是完整的,此时却被切割成活生生的和已被制成的标本;其三是诗的整体隐喻,说的是飞禽的标本,但隐喻的是柏林墙的制造者与维护者,这新的规则设定就给读者带来了全新的感受:切肤之痛跃然纸上。诗人为创新而设定的新规则往往是要付出沉重的代价,那就是因为读者的惯性思维会在一个时期拒绝诗人所设定的规则,如朦胧诗刚兴起时横遭批判与围攻,甚至一些知名的老诗人也加入了唾骂的行列。对此,抽象派绘画大师,也是大理论家康定斯基有一个绝妙的比喻。他说,那些有创见的艺术家如同站在一个锐角三角形顶端的人,顶上为最窄小部分,依次下来越来越宽。由于广大观众和读者都处于三角形底部,他们与艺术家有着极大的距离,他们之间存在着较大的隔膜,艺术家的创新不仅不被他们理解,反而对他们怀着敌意。他以贝多芬为例,在他生前很长时间就被人们说成是疯子、骗子。梵高也有着类似的命运,此时艺术家的命运是孤独的。诗人在诗歌中设定性规则如何被广大的读者所认同?一方面是诗人要有强烈的视读者为上帝的愿望,诚如福斯特所言:“你必须常常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你的读者身上,这就构成了技巧。”同时也希望读者不断提高自己的欣赏水平,“做一个合格的读者”。另一方面,诗评家的类似中介的阐释必不可少,它有义务帮助诗人与读者愉快的对话中认同规则而签定“契约”。
七、诗歌中的音义对应
在古代,音乐、诗歌、舞蹈是共生的,只是以后才逐渐分化并各自独立,也因有了这番姻缘,独立后的诗歌也就有了音乐的烙印,那就是诗歌语言要讲究节奏与韵律。然而这一特色似乎被不少人忘记了,认为喊出来并将它分行变是诗,以至使诗人公刘感叹:“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还多。”
那些有创见的诗人总是发掘并强化他诗歌中的音乐因素,努力寻找到语词和精神生活密切结合的效果,在他们的诗中,声音和意义是密不可分的对应。如李清照的《声声慢》历来为人们所称道,就因为它开头连用了七个叠字:“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由于这些叠字多为齿音、舌音和叠音,一种浮躁不安、无所适从、飘荡无定的心理状态由此被生动显现了,在我们面前似乎站着这样一个女子,她为了排除寂寞正漫无目标地东寻西找,其结果什么也找不到,这更加深了自己的寂寞与苦闷。在新诗中,诗人们也不例外地为寻找这种音义对应的途径而竭尽全力,常见的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拟声
在音乐中,拟声也是表现艺术形象的手段,中国民乐《百鸟朝凤》就模拟多种鸟的叫声,美国作曲家格罗菲的《大峡谷组曲》中第三乐章“在山谷小径上”最为听众喜爱,就因在这一章中,作曲家在演奏中模拟了驴子嘶叫声,土人吹笛声,流水声,以此表现出大峡谷特有的自然景色与浓郁的地方风情。
在诗中也同样有拟声,如蒲风的《茫茫夜》中就以“沙……沙……沙”、“号号号”、“汪……汪……汪”、“轰隆!轰隆!轰隆!”等象声词模拟雨声、风声、狗叫声和雷声。再如傅天琳的《秋雨声声》中的“窗外的雨声/淅淅沥沥说个不停/窗内的语声/叽叽咕咕说个不停,”就是对雨声和说话声的模拟。
(二)、以特定的韵部表达所要表达的情感。在音乐中,不同的调式可以表达不同的感情,在诗歌中,不同的韵脚也有着抒发某种特定感情的功能,如郭沫若的《凤凰涅槃》中的凤歌,为表现男性雄壮悲愤的强音,用的就是十三辙的“灰推辙”。诗中说:“你是有限大的空球?/你是个无限大的整块?/你若是有限大的空球那拥抱你的空间/他从那儿来?”为表现女性的哀怨,凰歌用的就是梭坡辙:“五百年来的眼泪倾泻如瀑。/五百年来的眼泪淋漓如烛。/流不尽的眼泪,/洗不尽的污浊,/浇不尽的情炎,/荡不尽的羞辱……”
(三)、移情与联想
我们知道,音乐是诉诸听觉的艺术,它是不可能用来表现如大小、高低、远近、粗细、曲直、黑白、明暗、硬软、香甜等视觉、味觉、触觉等感受的,可是由于人们对不同事物的比附所起的联想作用,因而人们头脑中甲事可以转化为乙事,在心理学称之为移情。如儿童歌曲《小星星》,在钢琴伴奏中是常出现高音的连续波动的“颤音”,犹如星星在闪烁,听觉与视觉的通道被打开了。《和弦》一诗之所以给读者有很强的音乐性的感受,原因也就在此:
树林和我/紧紧围住了小湖/手伸进水里/搅乱雨燕深沉的睡眠/风孤零零的/海很遥远/我走在街上/喧嚣被挡在红灯后面/影子扇形般打开/脚印歪歪斜斜/安全岛孤零零的/海很遥远/一扇蓝色的窗户亮了/楼下的几个男孩/拨动着吉他吟唱/烟头忽明忽暗/野猫孤零零的/海很遥远/沙滩上/你睡着了/风停在你的嘴边/波浪悄悄涌来/汇成柔和的曲线/梦孤零零的/海很遥远
诗题为“和弦”,它告诉了读者,此诗借鉴了乐曲中和弦的做法。为表现处于文革中人们的孤独心情,这首诗每一节最后两句就有了类似乐曲中的副歌,它既有重复又有变化,它构成了类似乐曲中一组四个音符、横跨了八度的七和弦。此外在全诗中只有两处用了标点,即“楼下,几个男孩”,“沙滩上,你睡着了”,因此在全诗的大语境中就起到了切分音的作用,音乐上的切分音是指乐音由弱拍或弱位延续到一个强拍或强位的过程。通常是将任何一拍分为两个音时,其前边的音强,后边的音弱,但这种强弱关系有时会因需要而改变,较弱部分的音持续到后边的强拍上,使较弱部分转为强声的节奏形式。再之,全诗的结尾处多数用了弱音节,如“水里”、“街上”……由此它突出前面的字,恰好地表现出主人公那种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尽的无限惆怅。
八、模糊体验:音乐与诗的桥梁
音乐与诗的联系决不只是上面那几种,这里再以常为人们所忽略的诗与音乐共有的模糊体验并以杨炼的《蓝色狂想曲》作一说明。
这首诗的主导意象是“高高耸立岩峰上/我的白桦树”,它是诗人的自我。通过他的视角,从纷繁变化的意象群中看到梦汇总两个对立的世界:“光明与黑暗。”一边是少女们走出金色的贝壳/在清凉的月光下歌唱,“天空是美好的,海水是宁静的”,它是那样令人神往,可是在另一边“在那儿,一只小船的尸体/静静地载着遥远的风景/帆曾象征狂欢的孩子/在大海的泡沫中嬉戏叫喊/就在那儿/时间鸣响衰老/我的梦落叶一样不可挽回的飘零”。两个不同世界犬牙交错明显地打上了文革中混乱印记,它以隐喻方式折射出诗人复杂的心态:向往美好,厌恶丑陋。虽极为愤懑,但决不失望,只要世界在变化着,它就有希望:
世界的色彩在它的脚下变幻
就在这儿在无数飞逝的瞬息之间
它不感谢阳光也不伴随蝉的忧愁歌唱
只有生长证明自己的命运
虽然它只是诗人的一种模糊体验,但决非胡涂,而是因有太多的体验不能以概括性的语言予以一一命名。语言学家乔姆斯基认为用语言表达内心体验是又深层结构逐步向表层结构转换的过程。深层结构是思维最初刹那间在脑海中一组组具象事物的动态印象。美国诗人金斯堡就有这样体会:“从乳腺癌病毒到摇摆舞影视这样一些压根毫不相干的事会突然反射在大脑的屏幕上……谁也不明白,下一瞬间,什么念头会在头脑中浮现,或许与此同时廷巴克图有关,或许是热狗,夹笔眼镜、或照相机。”按乔姆斯基意见,当体验由深层向表层转换时,它实际为语言的编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共时呈现的印象就会被迫改编为一个线形序列呈现,它要求按语法规则将一串名词动词形容词的组合形成顺序排列。为表达出清晰的时空和因果关系,还不得不加进如果、因为、象、虽然、就、在、的等等连词、介词、副词、助词,以此表示“逻辑链”的成分参与融会。这就经常不得不削足适履而有着极大的意蕴损耗,它显然是诗人所不愿意的。这首诗的巧妙之处就在于诗人将自己的模糊体验叠加在同时模糊体验的交响乐《蓝色狂想曲》曲上。也就是说,诗人在这首诗中模糊体验如同他在欣赏格什温这首名曲所体验到的一样,都是纷繁复杂而绚丽多彩姿而难以一一界定。一位音乐评论家如此描绘他听《蓝色狂想曲》的感受的:“乐曲一开始,独奏单簧管在低音区惶惶不安地奏出颤音,忽然它象坐上了火箭,一下子就从地面上直冲九宵,吹出一段带有爵士乐味道的切分音主题。于是各式各样的主题就象湍急的水流,争先恐后地奔涌而来”。乐评家说的就是一种模糊体验。黑格尔说:“由于运用声音,音乐就放弃了外在形状这个因素,以及它的明显的可以眼见的性质。”它只能通过听觉由联想的方式调动大脑中原有生活图景中种种物象的库存。就以家喻户晓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为例。作曲家从民间传说中择取“草桥结拜”,“英台抗婚”,“化蝶”三个情节对应乐曲中的显示部、展开部、再现部,听众被感动了,但谁又能说他从中看的了环环相扣的完整的故事画面,只能是一种模糊的体验。
音乐与诗歌这种模糊体验,与其说是它的特点,不如说是它的优点。当体验由平行的共时状态被迫按语法规则变为一种“线形的序列”,脑海中最初丰富印象也就形销骨立。模糊体验的最大长处在于它的开放的状态给听众读者以鲜活的感受并形成二度创造。
九、陌生化
诗歌虽是语言艺术,它有别于日常语言。日常语言是一种实用语言,它无时无刻都在使用,就有自动化性质,它的司空见惯,也就钝化了人们的感受,我们的感觉常处于麻痹状态。诗歌语言则不同,为了给读者以新鲜感,它常以反常的方式出现,即对见惯的实用的语言实施阻挠、变形、扭曲的特别处理,使原先熟悉变成不熟悉的,需要重新加以审视。它就是俄国文艺理论家什克罗夫斯基所主张的“陌生化”,也可称为“反常化”。他说“艺术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人感觉事物,而非已知事物,艺术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的长度,因为感觉过程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
如何造成诗歌语言陌生化,可以有以下两种方式:
一是创造出日常语言中没有的新的词语,或旧词新用,如李纲的《蓝水兵》:
蓝水兵/你嗓音纯得发蓝,你的呐喊/带有好多小锯齿/你要把什么锯下来带走/你深深的呼吸/吸进那么多透明的空气/莫非要去冲淡蓝蓝的咸味的风。
嗓音发蓝带有锯齿,这是闻所未闻,用呼吸的空气去冲淡海水更是石破天惊,它生动地传达出士兵以特殊的感受对大海的眷恋之情,虽然有悖于日常的语义逻辑,但诗人的超常体验是可以被读者所领会的。
在被称为朦胧诗的作品中,上述用法更属常见。如“在颤抖的枫叶上/写满关于春天的谎言/来自热带的太阳鸟/并没有落在我们的树上/早晨,阅读我的皱纹/书打开在桌上/瑟瑟作响的,好象火中发出的声音。”
对这些被扭曲变形的语言,读者无法跃过它,否则准将一无所获,只有当你把它视为诗歌语言时,你就会从一个新的角度去感受眼前的世界,并从而惊叹诗人对世界的独特发现。
二是突出诗的韵脚以显示与日常语言的区别。如徐志摩的《残诗》:
怨谁?怨谁?这不是春天打雷?
关着锁着,赶明儿瓷花砖上堆灰!!
别瞧这白石阶儿光滑,赶梦儿,唉,
石缝里长草,石板上青春的全是霉!
那廊下的青玉缸养着鱼,真凤尾,
可还有谁给换水,谁给捞,谁给喂?
要不了三无天准翻着白肚鼓着眼,
顶可怜是那就个红嘴绿毛的鹦哥,
不浮着死,也就让冰分儿压一个扁!
让娘娘教得顶乖,会跟着洞箫唱歌,
真娇养惯,喂食一迟就叫人名儿骂,
现在,你叫去就剩空院子给你答话!
尽管这是首未完成的残篇,人们还是喜爱它,原因是不仅有密集的尾韵,甚至还有句中韵:“怨谁怨谁?”、“关着锁着”、“换水”、“给喂?”。它带来的音乐效果就与日常语言的散文化有着极其鲜明的区别。
我们认为在诗歌中的陌生化更应体现为社会关系中的人与人之间的新发现,体现出诗人对社会特别关注。如车前子的《日常生活》,此诗的副标题为“一个拐腿的人也想踢一场足球”。它写出了一个拐腿的人在观看世界杯足球赛时的心态。虽然残废了,但他却想也能踢一场足球,和正常人一样结婚生子,甚至在若干年后,“儿子飞跑在足球场上/就像我自己正跑着似的,坐在栅栏外/我温情地观看/阳光金黄/草坪碧绿/射门:我儿子就像我/把一个个字填进格子一样自然”。然而当他的手触及以自己“枯萎的右腿时,”他知道不过是一场梦幻。此时,他真忍不住要哭上几声。这时的读者不免一惊,在惊谔之余必然重新审视这一现象,我们对残疾人是否了解得太少了。眼前这个熟悉的人,一下子就变得陌生了,他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由于诗人是以正常人和残疾人相互参照写出残疾人心态,它所起到的震撼效果是异乎寻常的。
十、佯谬:通感、荒诞、黑色幽默
佯谬,又称悖论,即是非而似,是一种表面上自相矛盾,但实质上却正确无误的表达。它在诗歌语言用运上常以反常的形式将一些表面上看起来毫不相干的事物与感觉嫁接在一起,但却是可信的,因为它以心理真实为依据,佯谬因层次不同而有通感、荒诞、黑色幽默不同的表现。
先说通感,它是指一种感觉兼有另一种感觉的心理现象,是感觉相互作用或挪移的特殊表现。如余光中的《音乐会》:
音乐如雨
音乐雨下着
听众在雨中坐着
许多湿透的灵魂
快乐或不快乐地坐着
没有人张伞
欣赏音乐只能诉诸听觉,天下雨属视觉,而“音乐雨下着”,则是听觉沟通了视觉。
比这更怪异反常,但却传神的诗句却是洛夫的《金龙禅寺》:
晚钟是游客下山的小路
羊齿植物沿着白色的台阶
一路上嚼了下去
晚钟的声音属听觉,此时却转为视觉,成了指示牌,逶迤而下羊齿植物诉诸视觉,此时又转为味觉与触觉。
诗人以这种超常搭配在于制造动态效果,再如他写的《边界望乡》:
望远镜扩大数十倍的乡愁
乱如风中的散发
当距离调整到令人心跳的角度
一座远山迎面而来
把我撞成严重的内伤
远处的山居然可以在望远镜中把自己撞成严重的内伤,这是不可思议的,它由视觉转为触觉;可是诗人的思乡之情却由此凸现了。
佯谬的高层次为荒诞,它指的是那些和理性常态截然不同的表现,是一种变了形的心理真实。如三毛的《他和烤鸭》:
烤鸭蜷缩在盘子里
他蜷缩在酒店里
烤鸭摆在他面前
他摆在老板面前
烤鸭瞑想着春江水暖
他瞑想着南方温柔的妻子
窗外是另一个世界
下着雪
诗中的主人公内心极端孤独,刹那间便将自己和面前的烤鸭等同起来,既形似又神似,是内在孤独引起的错觉。这种荒诞在夏宇的爱情诗中有着意想不到的奇特效果:
把你的影子加点盐
腌起来
风干
老的时候
下酒
这太荒诞了,影子怎么可能腌起来风干?如不这样写,又怎么能表现出这位女子对情人移情别恋后的那种既恨又爱的刻骨铭心呢!这不就是爱的辨证法吗!
荒诞的极致形式便是黑色幽默,它以喜剧形式表现出生存处境的尴尬,一种苦涩的笑。如李亚伟的《中文系》,在诗中,诗人写出大学中文系的一些老师们的因循守旧和委琐浅薄:教材是几十年一贯制,他们的观念仿佛是出土文物,一个个都是五十年代的“活化石”。
中文系是一条撒满钩饵的大河/浅滩边,一个教授和一群讲师正在撒网/要吃透《野草》《花边》的人/把鲁迅存在银行,吃利息/当一个大诗人/率领一伙小诗人在古代写诗/写王维写过的那块石头/蠢鲫鱼或傻白鲢在期末渔讯中/挨一记考试的耳光飞出门外/老师说过要做伟人/就得吃伟人的剩饭背诵伟人的咳嗽……/教师如此,学生们更是一群玩世不恭的“嬉皮士”:
二十四岁的敖歌已经/二十四年都没有写诗了,可他本身就是一首诗/永远在五公尺外爱一个姑娘/由于没有记住韩愈是中国人还是苏联人/敖歌悲壮地降了一级/他想外逃/但他害怕爬上香港海滩会立即被警察抓去考古汉语/力夏每天起床后的问题是/继续吃饭还是永远/不再吃了/和女朋友卖完旧衣服后/脑袋常吱吱地发出喝酒信号……
这里的幽默就如同传统相声中的表演,内心悲苦已极,但却嬉皮笑脸。诗中的老师和学生如此思想贫乏,岂不令人可悲。
十一、整体与空白
刘湛秋的《大自然之恋》(二十一首):
骚动的沙滩/猩红的夜晚/海水忽然变成了酒,月光醉了/山峰却远远地后退越发幽暗/沉默的鱼群/不安的游人/礁石上刻着猜不透的由骨文/享受秋天享受最后一丝余温
这是一首歌颂大自然风光的诗,意象诡奇动人,似是一幅旅游胜地的素描,既有旖旎风光,又有悠久历史文物古迹。可是当我们读完全诗后,就会感受诗人在赞叹美丽景色之后的隐忧,那就是如何保持它的生态。就每一句话而言,看不出以上题旨,可是当这八句合为一个整体时,这题旨就作为“新质”从中显现出来。格式塔心理学家认为它是整体化产物。
正因如此,他们认为当一个不完整的形出现在人们面前,此时头脑中就会产生将它恢复成完整形的创造冲动力,力求将它恢复为完整、对称、和谐,他们称之为“完形趋向律”。当我们在读一首诗,如果出现了“空白”,我们同样有上述心态。我们知道这空白经常是诗人有意设置的,如力虹的黑蝴蝶,诗中隐藏了一个故事:因房屋拆迁,主人公在整理一堆书信并准备付之一炬时,记忆之网拉开了:
你亦向我走来/你幽怨的目光如火焰灼痛我的手/你是谁/你在什么地方认识我/好象是在一个春天/花都开了/你到山区来看我/后来因为什么不再写信/因为什么别你而去我都记不清了/只有你幽怨的目光一直在远处闪着光亮/信已烧尽/炉火渐渐暗淡/你目光又化作无数只黑蝴蝶/飞翔于一堆纸灰之上/飞翔于感情和生命检验之上……
虽然在它后面有一个类似“梁祝”的爱情悲剧。它究竟如何造成?误会,父母作梗,移情别恋?诗人给读者留下一片“空白”,让人们在想像中驰骋吧。再如伊蕾的《独舞者》:
心灵的苦难伸出舌头
从指缝间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