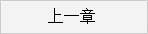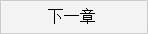蝉
大约六七天前吧,我在老校校园里听到了今年夏天第一声蝉鸣,心底涌起了一股久违的清凉与感动。
蝉实在是可怜又可爱的小生命。我总是固执的认为,只有在蝉鸣之后,夏天才算真正到来。而这人世的夏天,却是它们短暂生命的春天--最初的,也是最后的;它们确乎是不知春秋的蟪蛄之流。据说蝉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地下度过,蛰伏期最短要三年两载,最长则有十三乃至十七年。然而奇妙的是,无论如何,这个数字总是素数,因为它们要躲避自己的天敌,而素数年的蛰伏期与天敌同时出现的概率最小--大概它自己也知道这短暂的光明来之不易,才会如此惜命吧。蝉有许多名字,但都极其平凡甚至恶俗,我愿意给它一个“三生虫”的称号,方不辜负它数载于地下的苦寒与期望。
蝉是古典文学中一个重要的意象,尤其是在文学的自我觉醒之后,由单纯的咏物对象而被赋予了太多文人的自我况味与感受。现在能记住的关于蝉的诗,只有虞世南的《蝉》、骆宾王的《在狱咏蝉》及李商隐的《蝉》,而“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则分别言清高清白清贫,借蝉之高洁自剖方寸罢了。文人眼中的蝉,是如同不食人间腐朽的鹓雏,只靠几滴清露、一阵西北风和一点清高之气而存活的象征,是宁肯香抱枝头而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
古人有一种天真可爱的迂腐之气,往往爱给一件平常的事情赋予不平凡的含义,然后发一通扯心扯肺的感慨。如看到一种叫蜾蠃的虫子将螟蛉的幼虫负到自己的窠里去,便认为是代人育子,《诗经》里就深情赞叹“螟蛉有子,蜾蠃负之”。信古而不疑的后人,被先人的细致观察所震撼,为蜾蠃的拳拳大义所感动,忘了去追究蜾蠃负螟蛉之子的动机,以后直接将养子称为“螟蛉”。到了近代,事事讲求证据真理的西方科学家们,通过更细致入微的观察发现,原来“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是为了带回家给自己的孩子当零食,而绝非高尚的“哀哀父母”,古人若是知道了这一节,当做何感想。穷根究底的科学家又发现,“垂緌饮清露”的蝉也并非君子,它的若虫在地下靠吸食树根的汁液生存,而成虫则吸食树干的汁液--总之人心不古之后,蝉心也败坏了。但我不肯相信那些理性万分的分析,觉得蝉仍是可爱的益虫。
许多年前,至少也得有十年了吧,孩提时代的我最喜欢的季节就是夏天:不为可以天天放开肚皮吃西瓜,也不为可以天天去河里洗澡撒欢,只为能够听到蝉鸣,可以去逮蝉。每年蝉鸣第一声的时候,我就开始央求妈妈带我去逮蝉,妈妈总是哄我说,“现在蝉太少,等过几天多了就带你去。”可是急躁的心总是耐不住那几声蝉鸣,没过几天,我便又去央求妈妈,她则用她的老把戏再骗过我几天。在一次次的请求与敷衍里,夏天就过去了。终于在某年的夏天,我再次提出之后,妈妈居然答应了。当时我真是高兴坏了,颇有当年范进先生得知自己中举后的风范,用妈妈的话说就是“丢了魂儿”似的。那天晚上比许多年后更彻底的明白了什么叫辗转反侧,孤枕难眠。
第二天早上改掉了以往赖床的毛病,天没亮就催妈妈赶紧准备出发。妈妈说,你急什么?现在太早,露水太重,粘不了知了的。我们那儿管蝉叫知了,逮知了叫粘知了。逮知了需要用到一种自制的“面筋”,具体的制法是用水将面粉淘洗,洗净了面粉里的淀粉后,剩下一团软软粘粘很有弹力的东西,就是面筋。不要小看这一小坨东西,它可比胶水黏性还强。将它仔细缠在一根长竹竿的细头上,人站在树下,将裹着面筋的竹竿小心翼翼的对准蝉的翅膀,轻轻一戳,要是听到一声凄厉的哀嚎,一团黑乎乎的东西在竹竿顶端拼命的抖动,就知道俘获了战利品。逮住的知了,要轻轻的从竹竿上摘下来,不能让破碎的蝉翼留在面筋上,否则会影响后面的使用效果的。摘下的蝉,用针线穿起来,随手提着。技术好的话,小半天下来,可以逮上百只,哇啦哇啦的叫着,简直是“听取蝉声一片”了,实在是壮观而令人满足。后来学古文,大概是《庄子》的篇目,有一篇叫《伛偻承蜩》,讲的就是驼背老人逮知了的故事,两千多年前所用的方法和我们那儿现在用的几乎一模一样,连孔夫子都对他的技术赞叹不已。篇末夫子照例有一段鞭辟入里的微言大义,可惜我记不得了,只是当时对老人逮知了的技术极其神往,极想把他的手艺学来的,奈何余生也晚,做不了老人的关门弟子了。
蝉在成为蝉之前,它的若虫是一直生活在地下的。一般在雨后的第二天傍晚,成熟的若虫便纷纷破土而出,爬到附近的树上,到达一定高度后,便用带有倒刺的腿将身体固定在树干上,开始蜕皮嬗变。首先是背部裂开一道大约一公分长的口子,然后口子越裂越大,蝉的背部慢慢往外拱出,这时蝉的皮肉是特别柔嫩的,裸露在外面的身体一颤一颤的,慢慢的整个背部从壳里挤出来了。然后是头部,继而是柔软娇弱的腿,休息一会儿,便缓缓的将整个身子从壳里走出来,走向生命中最后也是最灿烂的时光了。蝉完全从壳里蜕出来,需要十多分钟,而刚蜕出壳的蝉只是一个淡白嫩黄的肉坨子,翅膀也没有完全展开,一副柔弱而任人宰割的样子,要过好长一段时间,身体才能由黄白转为浅咖啡色再转深最终成为黑色,在身体颜色转变的过程中,它的翅膀也在逐渐强壮,可以云霄一试了。三十六计中有一计叫“金蝉脱壳”,真是不得不佩服古人的观察力,远远望去,走失了蝉的蝉蜕和之前毫无二致。以前一直觉得,《红楼梦》里冷子兴演说宁国府那一回,居然没有说荣宁二府像“脱蝉之蜕”,不禁对雪芹先生缜密的想象力颇有瑜瑕之感。
当然,也有等不及金蝉从地里爬出来去捡的时候,通常会从家里扛一把铁锨,趁着父母午睡之后,偷偷溜到自家地头前的树下,极其仔细的将地面浅浅的铲一遍。如果有金蝉的话,地面上会出现一个大拇指大小的洞,往下一看,嚯,一直精神抖擞的金蝉正挥舞着大螯向人示威呢。这时就把一根手指头伸进洞中,傻乎乎的金蝉照例会用双螯夹住指头。金蝉个头虽然不大,但力气还是蛮足的,夹住指头颇有些疼,不过用这点短痛换来的长久欢喜,又算得了什么。将金蝉小心翼翼的从洞里提出来,装进身边的罐子里,继续投入到紧张而光荣的劳动中去。不过这种喜悦的时刻毕竟不多,有时候几十铲铲下去,地面平平整整,连个蚂蚁窝都没有;这时候就难免愤愤不已。记忆最深的是有一次一铲子下去之后,地面冒出来一个洞,想都没想就把指头伸了进去,碰到的却是一团软软凉凉的东西,心里一惊,赶紧收回手指,突然一只小蛤蟆从洞里跳了出来,当时又气又恼,用土块把它赶到地头的水沟里去了,从此以后对蛤蟆没有一丝好感:长得丑,还好意思出来败人兴。后来读沈复的《浮生六记》,才发现这不解风情的蠢物不仅给我的童年带来了不快,还将他当年的雅兴彻底败坏,及至读到“鞭数十,驱之别院”方稍稍解恨。
长大以后辗转各地求学,离家越来越远,自然是没机会逮蝉了--况且逐渐长大,心境已不似少年之时。幸好每年暑假可以回家长住,聆听故乡的蝉声,也算慰情聊胜无吧。离家的岁月,偶尔会在春秋季节的梦里,回到夏日的儿时,挥着满头大汗在田间的树下搜寻金蝉。梦里每一次都比当年收获的多,只是醒来后是无比的怅惘。去年夏天回家,一次偶然的机会,和几个儿时的伙伴夜里出去散步,意外地在村外的树上发现到一只金蝉。回到家后,妈妈看到手捧金蝉激动不已的我,笑着说我还是和小时候一样,对金蝉的迷恋不减当年。及至听说今年村外的树要砍伐,又着急那赖以生存的金蝉怎么办,没有树根的汁液,它们靠什么存活?新种的树苗要过数年才能长成,韬光养晦于地下的它们恐怕等不到那个时候了吧。或许以后回家,再也听不到蝉鸣了,或许它们真的要和我的童年一起随风飘散了吧。
壬辰闰四月廿二日
|